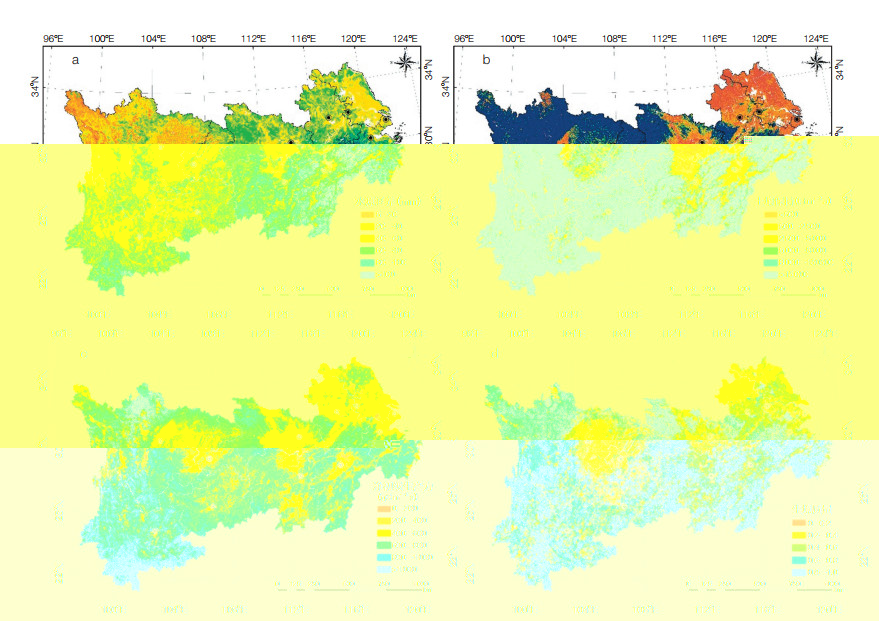2. 中国科学院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190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长江是我国第一长河、全球第三长河,国家战略水源地,以及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长江在维护我国生态和水安全方面的地位无可替代。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时期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形成国家“一体两翼”开发开放大格局的主干轴线。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定下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总基调。
长江经济带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但由于长期高强度开发的累积效应和缺乏科学的空间开发管控等,导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状况形势严峻。不仅长江水环境和水生态问题日益严重,干流局部岸段主要饮用水源地同危险品码头和排污口交错布局,岸边污染带不断扩大、水环境等级不断下降,水生生物种类和数量持续减少、多种珍稀物种濒临灭绝。而且长江流域上游山地生态退化与地质灾害频发,中游湖泊湿地萎缩、江湖关系紧张,下游河网水环境污染和湖泊富营养化不断加重,从而严重威胁长江作为国家战略水源地和重要生态支撑带的地位。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成为国家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和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根本要求。
本文依据长江流域及西南诸河水资源公报、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公报(1997—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等统计数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国控水质断面监测周报(2006—2018年)、生态环境部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日报数据(2015—2019年)、不同时相遥感解译数据、历史及长期专题研究积累的资料等,客观审视了长江经济带生态本底基础条件,深入剖析了长江经济带开发存在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总体策略,供相关研究和决策者参考。
1 长江经济带生态本底与开发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 1.1 长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不可替代,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水源地(1)长江是国家不可替代的战略水源地和清洁能源基地。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达9.6×1011 m3,约占全国淡水资源总量的36%,不仅满足了全国约42%人口生活、38%粮食生产和44%国民生产总值(GDP)产出的生产生活用水需要,而且还通过南水北调中线和东线等跨流域调水,缓解了华北地区城乡水资源短缺问题,并成为国家应对未来水资源安全的重要依靠。长江干支流水力理论蕴藏量达3.05×108 kW,占全国的40%;水力可开发量2.81×108 kW,占全国可开发量的53.4%。2018年长江流域水电发电量7.93×1011 kWh,约占全国的66.1%。
(2)长江货运量为全球内河第一。 2019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30.3亿吨,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 844万标箱,长江干线亿吨大港达到14个。近年来,长江干线航道得到有效治理,长江口深水航道全面建成,南京以下12.5 m深水航道实现贯通,5万吨级海轮可满载直达南京港。
(3)长江渔业不可替代。长江水系(包括湖泊)共分布鱼类378种,约占全国淡水鱼类总数的33%,居中国各江河鱼类资源之首,其中特有鱼类147种,占长江鱼类种数42%。长江作为我国淡水鱼苗种重要生产基地,盛产“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等经济鱼类;在我国主要35种淡水鱼养殖品种中,长江自然分布有26种,拥有如鳜、长吻鮠、南方鲇、胭脂鱼、黄颡鱼、中华倒刺鲃等许多珍贵、高值养殖种类。长江是我国最重要的淡水渔业种质资源库。
1.2 长江经济带生态区位重要,是全球重要的天然物种基因库(1)长江经济带天然物种资源丰富。上游地区:拥有包括森林、灌丛、草原、草甸、湿地、高山冻原等几乎所有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净第一生产力(NPP)高、生物多样性丰富;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持等生态系统调节和支持服务远大于供给服务,但生态系统相对脆弱;因此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集中连片保护价值高(图 1)[1]。中游地区:山地森林、农田和江河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类型占比高、分布广,生态系统调节、支持服务与供给服务重要性兼备。下游地区:农田和江河湖泊与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地位突出。
(2)长江经济带南北位置适中,其优越的光热水土配比条件,孕育了丰富的承南启北的动、植物区系,成为全球重要的天然物种基因库,极具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长江流域共有重要保护物种1 034种,包括植物568种、哺乳动物142种、鸟类168种、两栖动物57种、爬行动物85种、鱼类14种。此外,长江作为我国众多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繁衍场所和避难所,共有包括中华鲟、白鲟和长江鲟在内的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14种。仅三峡库区就有植物208科1 428属6 088种,中游地区有植物202科1 476属7 037种,下游地区有植物174科1 180属4 259种[2]。
(3)按全国生态功能区划,长江经济带涉及25个重要生态功能区,数量为全国的47.1%。其中,全国重要水源涵养生态服务功能区8个,包括秦巴山地、大别山、淮河源、南岭山地、东江源、若尔盖、三峡库区和丹江口水库库区等(图 2)。建有各类自然保护区1 066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数达165个(森林生态90个、野生动物47个,内陆水体14个、野生植物12个、地质遗迹和古生物遗迹各1个);保护区面积1.86×107 hm2,约占长江经济带总面积的9.1%。
1.3 经济带生态地理格局特殊,自然生态灾害类型多风险高长江经济带复杂多样的地质地貌环境和特殊多变的气候水文条件,导致以水灾和山地灾害为主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这些自然灾害成为长江经济带心腹之患。长江上游地区地处中国地势第一、二级阶梯交界处,地质条件复杂,高山峡谷型地貌广布,新构造运动活跃,地震和滑坡泥石流灾害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规模大,而且具有突发性、群发性和灾害链生效应,重大地质和山地灾害几乎连年发生[2]。
长江东西流向与雨带方向吻合,雨带停留时间长、多持续性暴雨,上游地势落差大汇流快、中下游地势低洪水蓄泄不畅,上、中、下游暴雨和洪水常常遭遇;加之流域水系发育,入江支流众多,且干流中游有卡口、下游河口有潮水顶托,导致长江尤其是中下游特大洪水频发,洪水灾害呈峰高、量大、历时长等特征。
1.4 水环境和大气环境污染严重长江经济带开发历史悠久,人口稠密、经济相对发达,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导致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大,环境污染累积效应显著,以水环境和大气环境质量下降为标志的环境问题突出。2018年1 261个重要水功能区中有21.1%未达标[5]。2006—2018年,长江干流25个国控断面中,9个断面的pH值、12个断面的溶解氧含量(DO)、16个断面的高锰酸盐指数(CODMn)和6个断面的氨氮浓度年均值呈上升趋势;2018年7个断面出现Ⅳ类及以下水质等级周数占比超过30%(图 3)。

|
| 图 3 2006—2018年长江经济带国控断面水质等级周数占比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06—2018年国控水质断面监测周报 |
(1)湖泊总体水质较差。 2018年长江流域61个主要湖泊中,Ⅰ—Ⅲ类水体面积仅占11.1%,Ⅳ— Ⅴ类占86.0%,劣Ⅴ类占2.9%[5]。鄱阳湖、太湖、巢湖、洞庭湖、滇池、武汉东湖、玄武湖、杭州西湖等湖泊,除杭州西湖整体水质为Ⅲ类外,其他湖泊水质均为Ⅳ—劣Ⅴ类。中、下游108个面积大于10 km2的湖泊中有95个(占总量88%)湖泊超过了富营养化标准,其中达到重富营养化标准的有25个(占总量23.1%),中营养和贫营养湖泊总计仅13个(占总量12%)[6]。
(2)大气环境整体堪忧。长三角、成都平原地区是中国霾日数最高的地区之一。其中,长三角大部分城市、成都市及周边地区的霾日数在50天以上,其中江苏及浙北的部分城市霾日数超过了100天[2]。126个地级市中76.2%的地级市臭氧(O3)年均浓度呈上升趋势,29.4%的地级市二氧化氮(NO2)年均浓度也呈上升趋势。2015—2019年大气首要污染物中细颗粒物(PM2.5)占比呈持续下降趋势,可吸入颗粒物(PM10)占比超过50%,O3占比呈持续上升态势(图 4)。长三角地区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氮氧化物(NOx)是我国甚至是全世界的一个高值区,由此引起O3等二次污染问题凸显。

|
| 图 4 2015—2019年长江经济带大气首要污染物占比变化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2015—2019年城市空气质量日报数据 |
(3)结构性、布局性风险突出,突发环境事件频发。沿江布局有62个工业园区,尤其是重化工企业密集分布,生产和运输的危化品种类多达250余种,全国40%的造纸、43%的合成氨、81%的磷铵、72%的印染布、40%的烧碱产能聚集在该区域,由此导致突发环境事件频发,严重威胁所在地及下游地区的供水与生态安全[7]。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共发生突发环境事件2 574起,约占全国总数的53.6%;其中,上海、江苏和浙江的突发环境事件占整个长江经济带突发环境事件总数的80%以上(图 5)。2013年以后,长江经济带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呈显著下降趋势,但重化工企业高密度布局的累积性和潜在性的环境风险依然很高。

|
| 图 5 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环境突发事件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8年 |
(1)长江上游水生生物退化快速,尤其是一系列梯级水电开发,导致珍稀和经济鱼类产卵繁育场和适宜栖息生境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三峡水库蓄水后的2003—2010年,三峡库区调查到特有鱼类23种,种数较蓄水前减少51.1%,三峡库区渔获物中特有鱼类优势度下降35.3%—99.9%;“四大家鱼”的产卵规模显著减小,中游监利断面“四大家鱼”鱼卵径流量年均2.28亿粒,较蓄水前1997—2002年减少90.0%。2011年开始实施的生态调度虽促使“四大家鱼”呈好转趋势,但仅占1997—2002年的23.9%(图 6)[8]。2003—2016年长江年均天然渔业捕捞量比1997— 2002年减少42.7%。云贵高原湖泊生物资源退化,土著物种快速减少;鱼类由高原鱼类区系向长江中下游鱼类区系演变,土著种显著降低。
(2)长江中下游湖泊湿地生态明显退化。长江中游鄱阳湖和洞庭湖洲滩湿地植被分布呈面积扩大、植被带下移和明显旱化的演替特征,导致候鸟栖息地发生显著变化;河湖鱼类种类快速下降、数量减少,洄游性鱼类几乎绝迹;螺、蚌等大型软体底栖动物大幅减少,耐污染水蚯蚓、水生昆虫幼体增加;浮游动物中大型枝角类、桡足类种群、数量减少,而小型的轮虫、原生动物数量快速增加;水生高等植物分布范围大幅度缩减,群落组成趋于简单,沿湖岸大型挺水植物消失,大量湖泊由清水草型湖向浊水藻型湖转变[9-11]。
1.6 以江河湖泊关系不和谐为代表的重大工程生态环境累积影响不断显现(1)大型水库群建设改变长江上游来水来沙情势,显著影响河湖水文、湿地生态、防洪与供水安全。近几十年来,长江经济带范围内各类水坝工程呈暴发式增长,仅长江上游以三峡为代表的在建与已建大型控制性水利工程就超过20座。大型水库群建设深刻改变了长江上游来水来沙情势,进而对中下游河湖水文和生态环境造成越来越显现的影响。2003年以来,长江上游来水量持续偏小,宜昌站2003—2014年有80%时间年份径流量小于1956—2014年均值。上游来水减少,中游坝下河道少水少沙,中游汉口站超半数年份径流量小于多年均值。2003年以来与1956— 2002年均值相比,中下游交界控制站大通站上游来沙占比由86%突降到37%。这一方面导致长江中下游河床出现了长距离、较为剧烈的冲刷,宜昌至湖口河段仅平滩河槽总冲刷量就达1.06×109 m3,其中67%发生在宜昌至城陵矶河段,河槽边滩刷深和堤岸崩塌时有发生,严重危及长江堤防安全;另一方面引起长江干流同流量下水位不同程度降低,导致长江对通江湖泊顶托作用呈趋势性减弱,对湖泊调蓄水能力与湿地生态平衡,以及中下游沿岸地区防洪、供水安全等影响深远[9, 10]。
(2)水利工程建设和围垦加剧江(河)湖关系渐呈不和谐状态。长江经济带不仅是我国仅次于青藏高原湖泊分布最集中的区域(面积大于1 km2湖泊数量和面积均占全国的25%),而且也是近百年来我国湖泊数量和面积变化最显著的区域[6]。历史上,这些湖泊大多与长江或其他河流自然连通,发挥着正常的洪水调蓄、水质净化、淡水供给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等生态服务功能。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为修闸建坝等水利工程建设和围垦活动加剧,该区域绝大多数湖泊失去了与江河的天然水力联系,江(河)湖关系渐呈不和谐状态。
(3)江湖阻隔加剧湖泊萎缩和生物多样性下降。 ①众多湖泊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因水文水动力条件突变而改变,江湖间水生生物联系被阻断,导致江湖(海)洄游性水生动物从原有分布湖区消失而日益濒危,湖泊鱼类河水生植物种类和数量明显减少。藻类尤其是蓝藻大量繁殖,底栖动物种类减少且趋于小型化,成为蓝藻水华暴发等生态灾害频发的重要原因。例如,2007年太湖蓝藻水华暴发,引起无锡城市供水危机。②加剧湖泊萎缩和围垦,导致湖泊数量和面积快速减少。仅20世纪50年代以来,宜昌至大通的长江中游地区湖泊面积就由17 198 km2减少到现在6 600 km2左右,减少了约2/3;长江中下游地区消失的面积1 km2以上湖泊数量占全国44.4%;五大淡水湖面积均显著减少,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面积分别减少了1 725 km2、2 267 km2和172 km2,直接引起湖泊调蓄能力大幅下降,导致小水大灾的被动局面[2, 10]。
(4)重大工程与气候变化影响交织,增加了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21世纪初以来,受气候干湿周期交替变化、三峡等长江上游水利枢纽蓄水运行和流域人类活动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洞庭湖和鄱阳湖现存两大通江湖泊水文情势发生深刻变化,湖泊枯水提前、枯水期延长、枯季超低水位频现,不仅严重影响湖区工农业生产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而且还危及湖泊与洲滩湿地生态平衡和候鸟栖息地生境退化,出现一系列连锁生态环境问题[9-11]。
2 保护总体策略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综合开发条件最好的区域,拥有南北适中、东西贯通的优越区位,得天独厚的水、土、气、生自然资源配比条件,较为完备的产业和城市体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是只保护不开发,而是要将保护摆在优先和突出的位置,不能以牺牲生态和环境为代价走粗放无序开发的老路,必须以“大保护”为前提因地制宜科学有序集约开发,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2.1 将长江水生态环境保护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率先实行水质目标管理(1)强化长江岸线和沿江产业与园区开发管控,实施入江污染物源头控制。把长江岸线占用管理作为规范沿江地区有序开发的核心抓手,将岸线陆域纵深0.5—1 km范围和岸外滩地纳入岸线范畴,遵循生态优先、集约开发和有偿使用的原则,实施长江岸线占用许可制度。严格沿江工业企业分散布局和重化工产业园区设置管理,限期清理和关停园区以外有污染的企业,改变长江沿江重化工业分散布局、污染和风险难以管控的局面。对在沿江地区设置的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强制建设高标准、全覆盖的污水处理系统,规范和严控长江沿岸排污口设置,确保无分散工业与生活污水直排,以及严禁入江支流达不到Ⅴ类标准的水体进入长江;并且,要对无法满足基本要求的岸段实行区域环保限批措施。
(2)强化长江干支流和重点湖泊水质目标管理。积极探索流域环境质量目标管理模式,率先实现长江经济带环境管理由污染减排目标考核向环境质量目标考核转变。
2.2 形成开发节约集约与生态自然开敞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1)加大生态系统完整性与连通性保护力度。以维持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服务和控制生态敏感(脆弱)区开发强度为重点,优化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图 7)[12],有效管控水电等工程开发规模和秩序,强化生态自然保育和河湖连通,建设以长江为主轴的水陆复合生态大走廊。
(2)强化国土开发生态指引,优化空间开发布局。结合岸线占用管控,合理划定生态、生活和生产空间,制定各类空间环境准入门槛和开发负面清单。实施严格的生态红线管控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强化重要城市群和省级及以上开发区集中集约开发,保护农业发展空间和绿色开敞空间。加快形成开发集中集约与生态自然开敞相得益彰、区域主体功能明确的国土空间开发新格局。
2.3 持续实施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保障工程(1)实施水安全保障工程。以长江源区和上游水源保护、中游水量合理调配和下游水环境保护为重点,强化水源涵养区保护;划定河湖保护红线,确保河湖面积不减少、调蓄能力不下降;开展退耕还湖还湿,严禁河湖滩地非法占用,限制蓄滞洪区开发强度,恢复和增加水资源调蓄能力;强化干支流水库群统一管理和优化调度,实施河湖连通和清水入江、清洁小流域建设,切实保障区域水安全[2]。
(2)实施自然生态保育工程。加强以长江鱼类资源保护为重点的水生态保护,严格控制长江洲滩湿地围垦开发,开展有利于鱼类保护的水利枢纽生态调度,以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长江水生态系统健康。
(3)实施重大灾害防御工程。划定长江上游地区地震、滑坡、泥石流等山地灾害风险区,实施高风险区移民建镇工程;加大陡坡地退耕还林还草、荒山丘陵绿化等生态工程建设,不断减缓水土流失危害;将长江及其干支流堤防加固与蓄滞洪区建设和长江干支流水库群联合优化调度有机结合,形成较为完备的长江综合防洪体系。
(4)实施环境生态风险防范工程。建立负面清单,构建严密的环境生态风险源分类监管和风险实时监控、预警与处置体系;推行环境信息共享,构建区域联防联控和应急响应机制;严格管控敏感岸段、区域污染企业布局和危化品运输。
2.4 打破部门和地方分割,实施流域综合管理(1)打破部门和地方分割,成立国务院直属的跨部门、跨行政区的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借鉴欧洲莱茵河和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经验,建立利益相关方共同协商决策的长江流域综合管理机制;着力解决各个行政主体单元和部门内部不能解决的跨区域、跨部门问题,统筹流域综合规划编制和空间开发一体化管控,监督《长江保护法》实施等。
(2)建立健全长江全流域自然资源保护管理、环境损害赔偿与责任追究及生态补偿制度。按照“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总要求,在长江经济带率先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登记、水电矿产水等自然资源有偿使用、资源总量管理,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资产损益评估考核机制;改变环境损害“企业赚钱、政府买单、群众受害”的现象,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和强制修复机制,合理合法追究环境损害责任;以国控或利益相关行政主体协商一致的控制断面关键水量和水质指标基准值为依据,将生态补偿、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相结合,根据关键指标与基准值的差值,建立健全流域跨界指标提升补偿和下降赔偿的流域上、下游双向补偿(赔偿)机制。
| [1] |
Xu X B, Yang G S, Tan Y, et al. Ecosystem services trade-offs and determinants in China'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0 to 2015.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8, 634: 1601-1614. DOI:10.1016/j.scitotenv.2018.04.046 |
| [2] |
杨桂山, 徐昔保, 李平星. 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廊道建设研究.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11): 1356-1367. |
| [3] |
生态环境部, 中国科学院.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2015-11-13].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g/201511/W020151126550511267548.pdf.
|
| [4] |
Xu X B, Tan Y, Yang G S, et al. China's ambitious ecological red lines. Land Use Policy, 2018, 79: 447-451. DOI:10.1016/j.landusepol.2018.08.037 |
| [5] |
长江水利委员会. 2018年长江流域及西南诸河水资源公报.[2019-09-03]. http://www.cjw.gov.cn/style2013/pdf/web/?file=/UploadFiles/zwzc/2019/9/201909031615548433.pdf.
|
| [6]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中国湖泊调查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
| [7] |
曹国志, 於方, 王金南, 等. 长江经济带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现状、问题与对策. 中国环境管理, 2018, 10(1): 81-85. |
| [8] |
Xu X B, Yang G S, Tan Y, et al. Unravelling the effects of large-scale ecological programs on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 of China's Three Gorges Dam.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256: 120446. DOI:10.1016/j.jclepro.2020.120446 |
| [9] |
杨桂山, 朱春全, 蒋志刚. 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11.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1.
|
| [10] |
Yang G S, Zhang Q, Wan R R, et al. Lake hydrology, water quality and ecology impacts of altered river-lake interactions:Advances in research o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Hydrology Research, 2016, 47(S1): 1-7. DOI:10.2166/nh.2016.003 |
| [11] |
胡春宏, 阮本清, 张双虎, 等. 长江与洞庭湖鄱阳湖关系演变及其调控.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
| [12] |
Xu X B, Yang G S, Tan Y. Identifying ecological red lines in China'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A regional approach.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9, 96: 635-646. DOI:10.1016/j.ecolind.2018.09.052 |